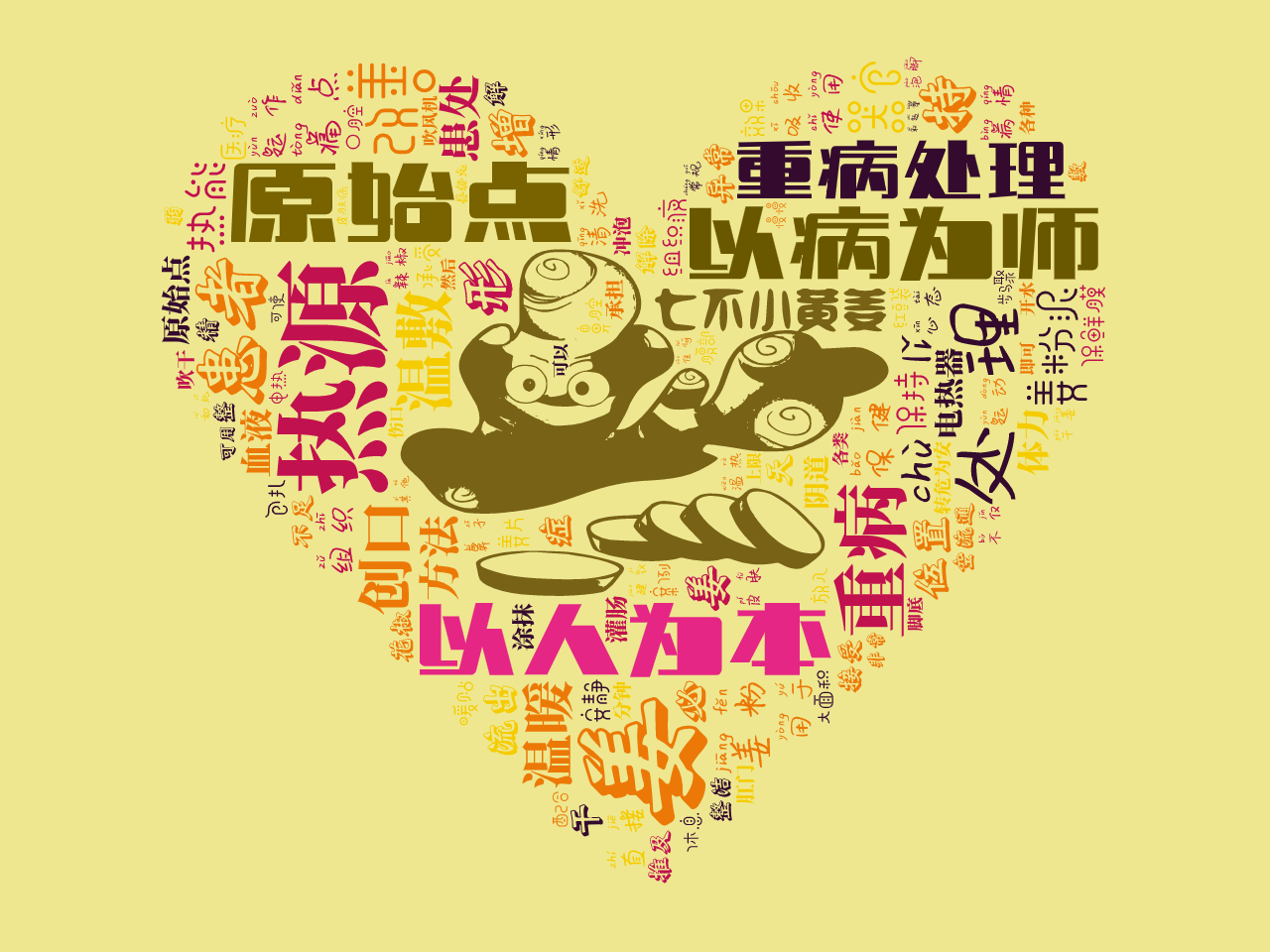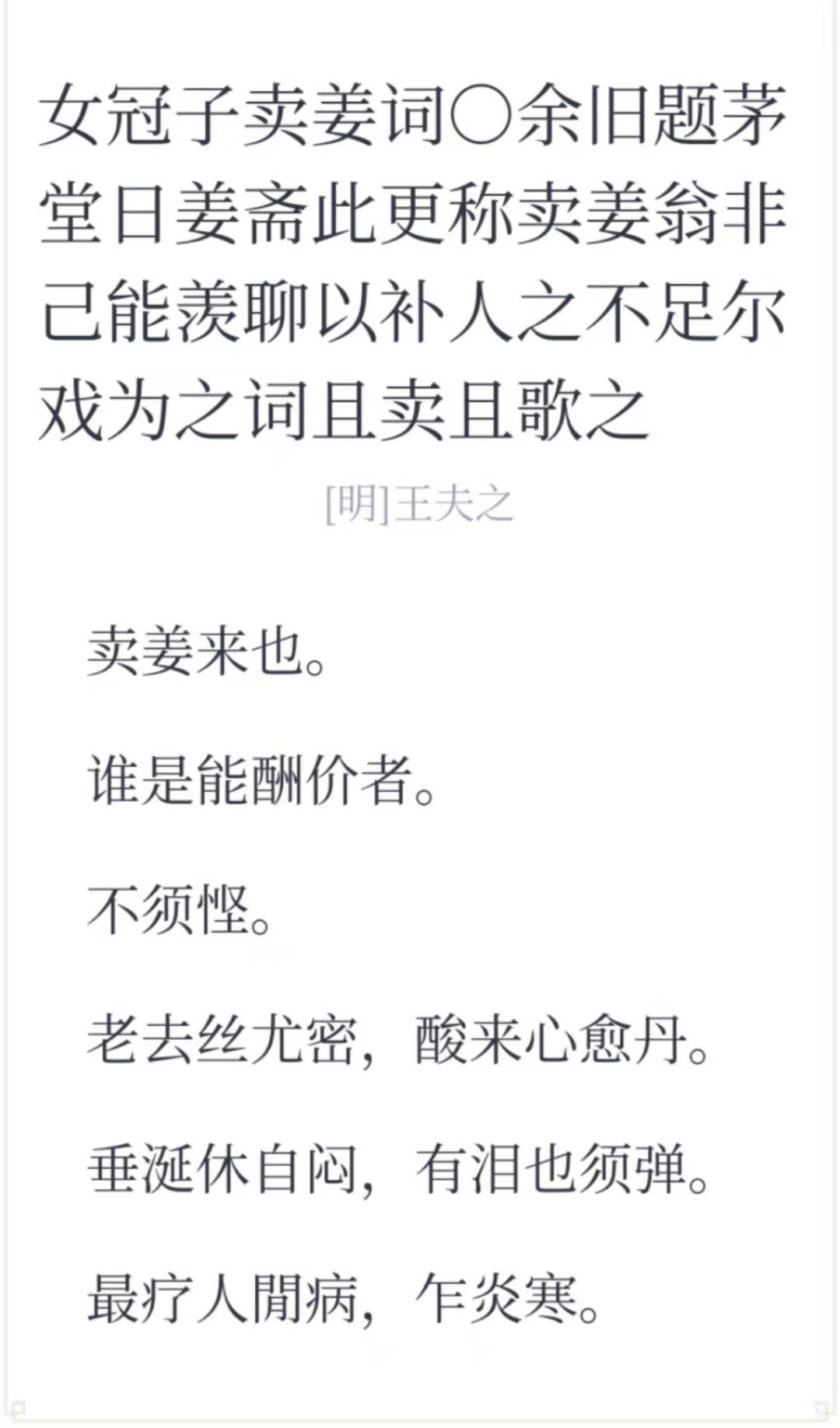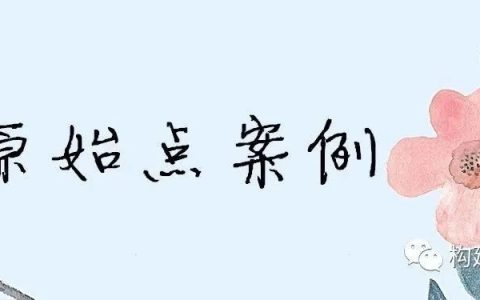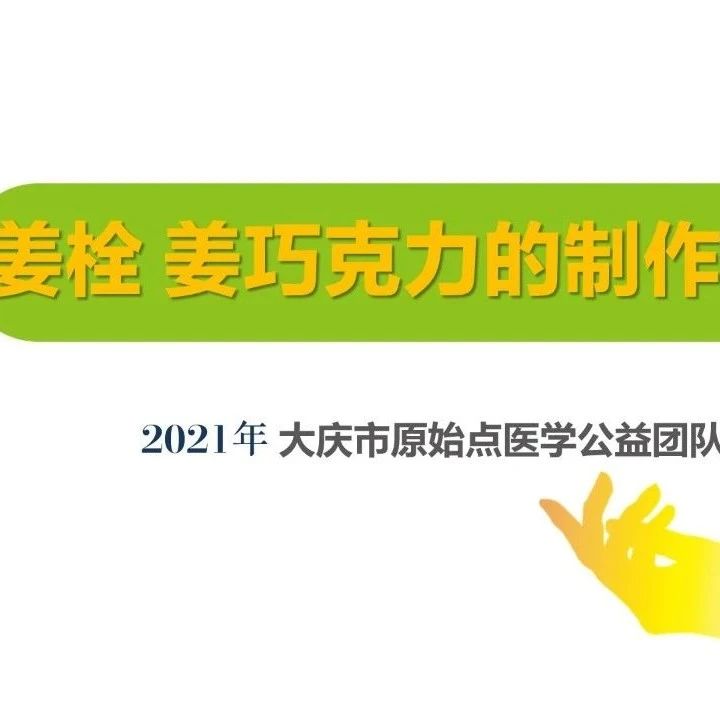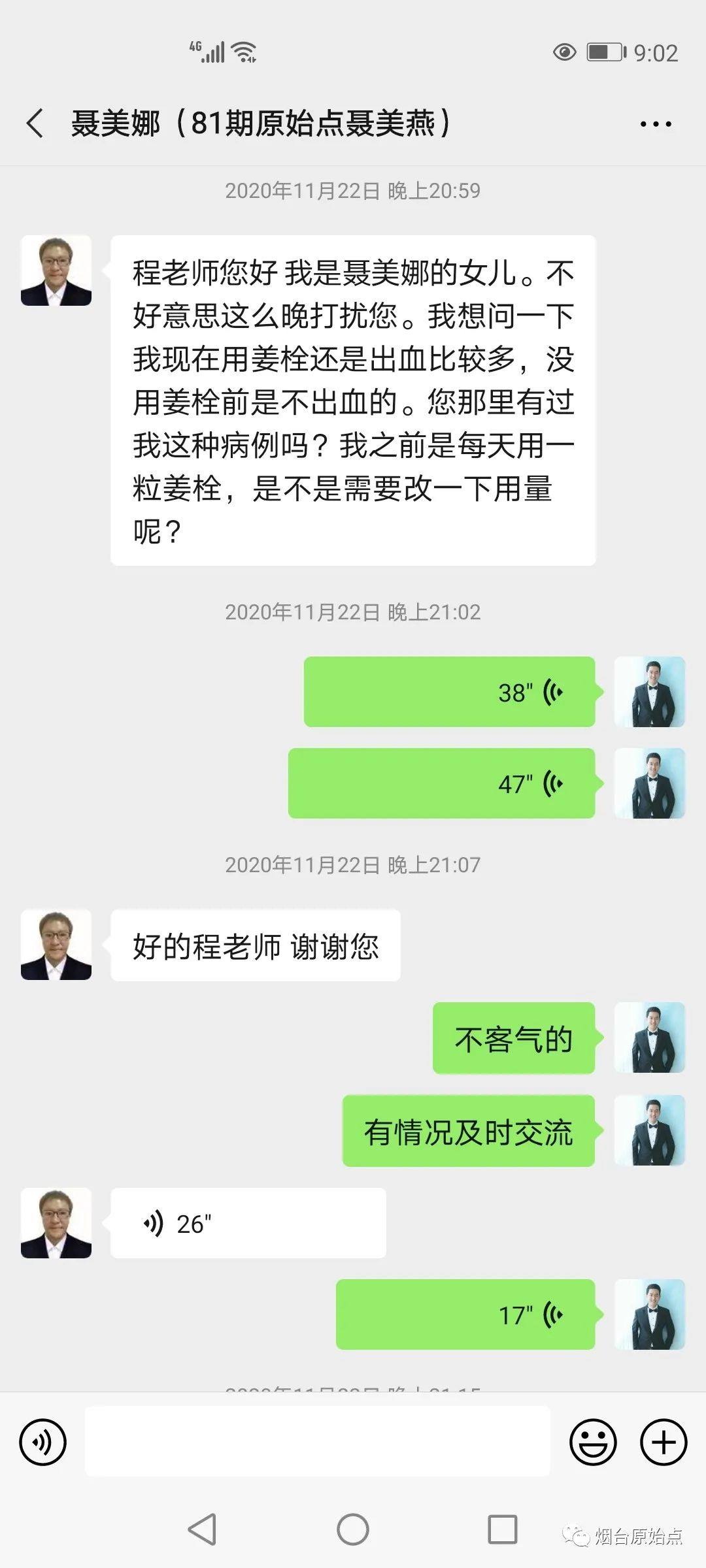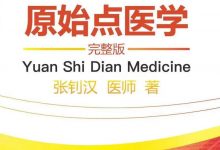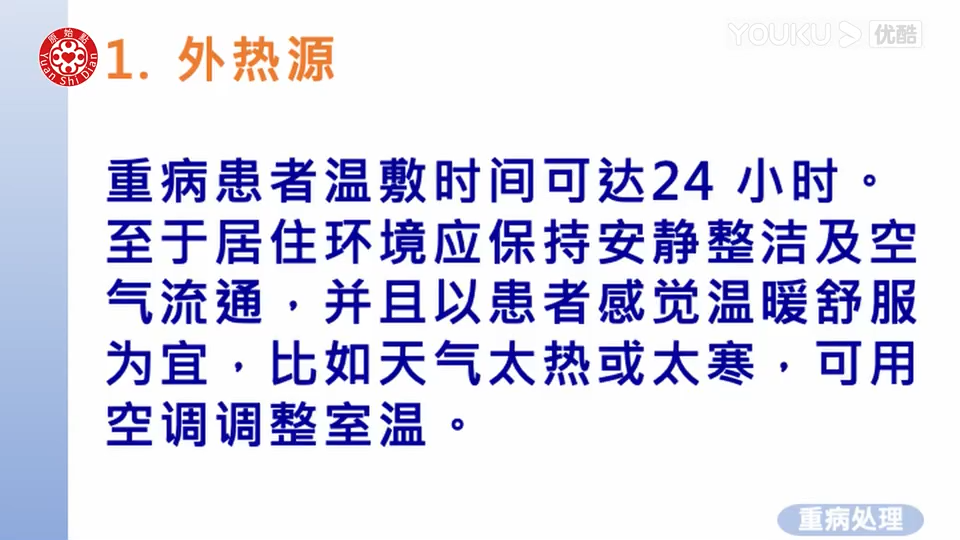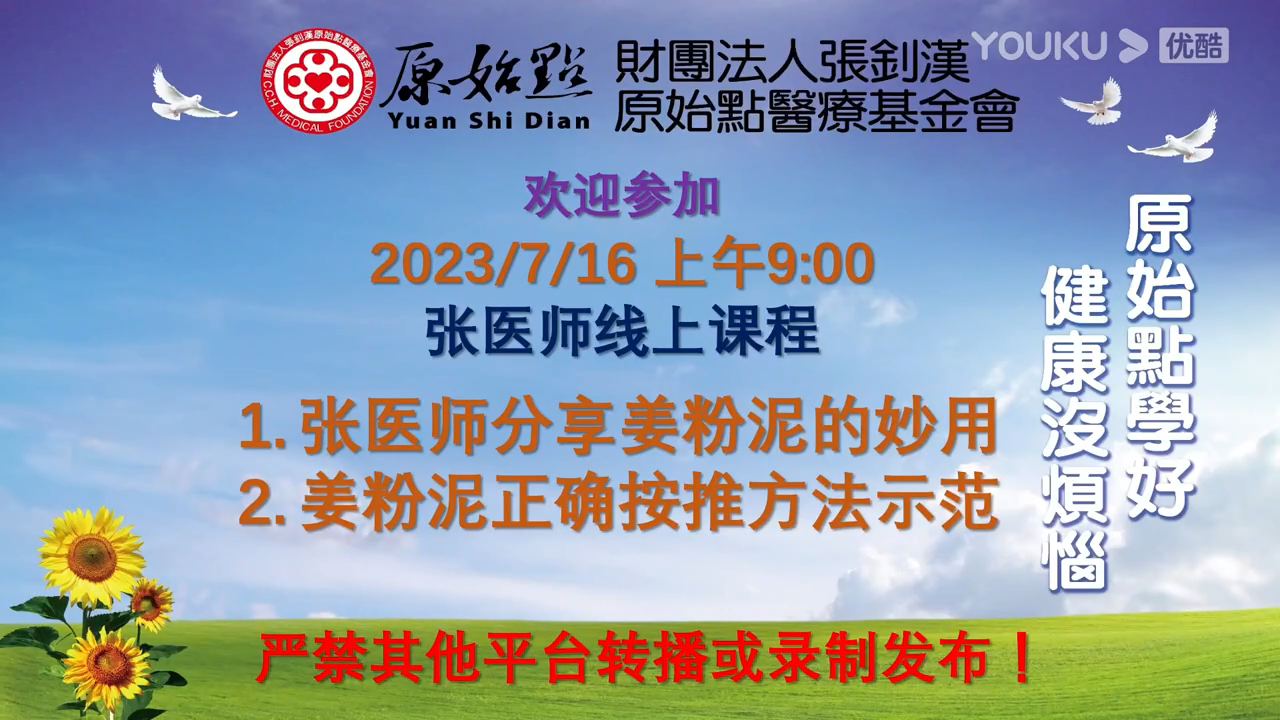2019年開始在黑龍江海倫市倫河鎮開發種植七不“寒地黑土富硒”香稻大米...2021年黑龍江海倫七不水稻基地實驗種植小黃姜。
七不”種植是明安農業、明德CSA生態姜園首創的良心生態農業種植理念。七不是指:不用化肥、不用農藥、不用農膜、不用除草劑、不用添加劑、不用轉基因、不殺生! 生姜養生不殺生,是符合戒殺生以惜物命,慎剪伐以養天和的自然之道。
明安心農人遵守踐行“但存方寸地,留與子孫耕”,” 一切福田,不離方寸;從心而覓,感無不通“的古訓。心地上用功夫,內外耕耘,用盡善緣,斷諸惡緣。順應天道與人心種姜做姜品。天時 地利 人和,因緣和合結善果!
明安心農人對自然敬畏,對人文生態精心呵護,關注鄉村,熱愛環保,與自然合作,以土地為生。明德惟馨、安生樂業!
袁隆平,因多器官功能衰竭,于2021年5月22日13時07分在長沙逝世,享年91歲。一位老者,一顆赤子的心,一個童真的夢,他對這片土地愛的深沉,他是稻田的忠實守望者!
致敬,緬懷!

據新華社記者從中南大學湘雅醫院獲悉,“雜交水稻之父”、中國工程院院士、“共和國勛章”獲得者袁隆平,5月22日13點07分在湖南長沙逝世,享年91歲。袁隆平是我國研究與發展雜交水稻的開創者,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成功利用水稻雜種優勢的科學家,被譽為“雜交水稻之父”。直到今年年初,他還堅持在海南三亞南繁基地開展科研工作。 時光倒流70年,袁隆平還是個農校的大學生。早晨愛睡懶覺,總是到緊急集合鈴了才騰地起身,鋪蓋也不疊,一邊扎褲腰帶,一邊往操場跑。同學們送他評語:自由散漫。 他打小貪玩,沒少挨父親板子。偏科很嚴重:喜歡地理、化學和外語,能拿高分,直到他成了年過八旬的老頭子,飆英文的習慣也沒改過;寫作文套用過“光陰似箭,日月如梭”,挨老師狠狠批過,從此再不愛用老八股;數學一塌糊涂,及格都得奮力掙扎。 最杰出的才華表現在游泳上,拿過湖北省第二名,可惜一次關鍵比賽前饕餮吃壞了肚子,被國家隊永遠地淘汰了。 幾十年后,他是中國殿堂級科學家。單位門口的大路乃至銀河系的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;有農民自發為他塑漢白玉雕像;盡管他本人再三強調不是熊貓,下至農民上自總理,都封他是“國寶”。 他的事跡上了小學生語文課本:雜交水稻之父——袁隆平。 南方周末2011年度盛典上,鐘南山院士為袁隆平院士頒獎,這段兩位院士罕見同臺的視頻,后被網友在2020年翻出來以致敬這對“醫食無憂”組合。 以下文章和訪談首發于2012年9月20日,今日重刊,以寄哀思。 袁隆平眉毛高挑,一笑起來更成了瞇縫眼,身板瘦而硬朗,愛穿個襯衣,扎進西褲里。他身體不錯,用行話說,叫“后期落色好”。最大的毛病是抽煙,一根接一根,喉嚨不大好。 雜交水稻培育成功后,“國寶”袁隆平再也自由散漫不成了。拿他倒苦水的話說:人怕出名豬怕壯。 被歡迎、被圍觀、被合影是生活的常態。他最怕興師動眾,偏偏每到一個地方,市長縣長什么的全出來迎接,“說我什么歡迎蒞臨指導呀,很麻煩”。不過面對蜂擁向他求合影求采訪的人群,他又總能揮著手淡定地hold住全場:one by one, one by one(一個一個來)。 2008年,袁隆平帶著老伴鄧則去逛車展,被一個“滿哥”(年輕小伙,湖南俚語)認出來,現場立馬炸鍋了。他在一輛奔馳敞篷車旁多流連幾眼,互聯網上就掀起了一場討論。不過持“仇富不仇袁隆平”的人占了上風,“別說買車,買飛機都理所應當”。 最后身家千億的袁隆平買了一輛5萬多的吉利熊貓,消息一出,網友被感動了。而這汽車的主要功用,不過是供他開車去離家1.5公里外的稻田查看水稻,平時根本不上街。 事實上,袁隆平對掙錢這事壓根不上心。他對財富葆有相當的平常心。很快,他把隆平高科的董事也辭了,埋頭搞他的科研,“我就是個過路財神”。 1930年,他生于一個書香世家。家里六兄妹,“隆”字輩,他排行老二,乳名“二毛”。 二毛在武漢念教會學校長大。很多年以后,這位農學大腕把這歸咎為一次誤會。那是小學一年級在漢口,老師帶孩子們去郊游,參觀一個資本家的園藝場。“花好多,在地下像毯子一樣,紅紅的桃子滿滿地掛在樹上,葡萄一串一串水靈靈的”。 農村給他的印象過于美好,直到1952年,他作為農學院的學生去土改,住進農民家了,才知道真正的農村“又苦又累又臟又窮”。 1953年,袁隆平畢業了,被分配到湘西雪峰山腳下的安江農校當老師。他在地圖上找安江,半天沒找到。他拿第一個月工資買了把小提琴,在偏僻的鄉下打發時間。 當時中國全盤學蘇聯,別人DNA雙螺旋結構遺傳密碼的研究都得諾貝爾獎了,中國還在學前蘇聯,搞無性雜交。 袁隆平說那時的自己是“迷途羔羊”,后來他就看孟德爾、摩爾根的遺傳學(當時的唯心著作)。孟德爾所發現的分離規律和自由組合規律,奠定了日后雜交水稻的理論基礎。 “最初搞無性雜交,鬧了許多笑話;搞小麥,沒前途;搞紅薯,感覺是個搭頭。轉過來開始研究水稻,一個偶然的機會,老天爺在我面前擺了一株特殊的水稻,讓我看到了。” 43歲這一年,袁隆平及助手育成三系雜交水稻,將水稻畝產量由300公斤提升至500公斤以上。這個中國自主產權的成果是世界范圍內的第一次。 1996年,他開始主持研究超級雜交水稻。他的目標是90歲以前,讓水稻畝產超過1000公斤。 他的理論基礎是,“如果我們能把光能利用率提高到2.5%,那么水稻畝產1500公斤是沒有問題的。” 2011年,他的攻關超級稻畝產達926.6公斤,2012年希望達到940公斤至950公斤。 潛增長越來越慢,袁隆平形容這是“矮子爬樓梯”,一點一點來。當旁人都為能否達到階段性目標緊張不已時,他卻一點也不介意對媒體笑嘻嘻地說:如果達不到,那牛皮就吹大咯。 2007年,袁隆平被授予“影響華人終身成就獎”等多項榮譽。他是個不愿退休的老頭子,日常行程是全國各試驗基地間飛來飛去,長期下地工作,被曬得像個非洲黑人,綽號“剛果布”。到了79歲那年,他說自己老了,終于開始戴遮陽帽下地了。 光環之外,生活中的袁隆平截然不同,詼諧且充滿自娛精神。他很介意自己被“高大全”了。在不啻于“成千上萬”次采訪中,他表現得像是個曝料的—— 別人恭維他會拉小提琴,他說:高手是后面彈鋼琴的,我是個南郭先生。 在長沙住了大半輩子,他如是介紹這座城市:北京是首都,長沙是“腳都”,四分之一的自來水都是洗腳水! 媒體一讓他談轉基因他就頭大,理由并非敏感話題,而是“我已經談了不下100遍了”。 有時老頭子來了興致,還拖住記者陪他一起打麻將,不賭錢,輸了的鉆桌子,“有一次他們想把我鉆桌子的鏡頭拍下來,可我身手麻利,一下子就鉆過去了。” 骨子里,比起商人和官員,袁隆平更像一個農民。“我不愿當官,不是做生意的人,又不懂經濟。” 功成名就后,有人勸袁隆平“退隱”,認為他完全可以“躺在功勞簿上”了。“我說不滿足,就算失敗了至少也還有教訓。”他說。 后來,這位科學家還是拗不過,被任命為湖南省政協副主席。許多大會小會,他情愿“躲”過去。前些年,每逢開會他就請假,以至后來每次通知他開會的政協工作人員主動發問:袁老師,這回請假嗎? 2012年“兩會”,他為農民提案。他提出《關于糧價的建議》:國家應該把石油補貼的錢補給農民,認為國家要對糧價政策作出根本性改革,建議以較高的價格收購農民的糧食,然后以平價出售糧食。 農民更愿意拋了荒去打工,農村空心化愈發嚴重。袁隆平也意識到現在學農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了。“我參觀過很多現代化的農業博物院,南瓜有幾百公斤重、甘蔗有兩層樓高,這些對年輕人有很大的吸引力,小學生也會感覺很有意思。”說這話時,他想起了童年參觀的資本家園藝場。 2012年8月31日,面對蜂擁向他的四家媒體,袁隆平第“N+1”次說起禾下乘涼夢:“我夢見我種的水稻長得像高粱那么高,穗子像掃把那么長,顆粒像花生米那么大,我和我的朋友,就坐在稻穗下乘涼。” 南方周末:1994年,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萊斯特·布朗出版了《誰來養活中國人》一書。他在書中預測:到2030年,中國人口將達到16.3億左右, 需要糧食6.51億噸,屆時中國糧食生產將下降到2.73億噸,需要凈進口糧食3.78億噸,從而引發全球性的糧食短缺和糧價暴漲。他得出結論,沒有哪個 國家能夠養活中國人。您對此怎么看待? 袁隆平:布朗,我在加拿大開會時曾經見過,他不認識我。我們吃飯時坐不同的桌子。布朗是出于好意,以一種Wake up Call(警世的呼喚)的精神,提出了一個現實的問題。但他最大的弱點,是對科技進步對提高農作物生產力的巨大潛力估計不足。他寫書的時候,還不知道我們中國要啟動超級稻計劃。 2011年,我們的糧食總產量是5.7億噸。國家發改委的數據則顯示,中國糧食庫存占消費的比重超過40%,大大高于聯合國糧農組織的17%-18%的糧食安全線。中國現在擁有1.5億噸至2億噸的儲備糧,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一倍。面對布朗先生的提問,我們可以鄭重地回答,“中國人不僅能依靠自己解決吃飯問題,而且還可以幫助發展中國家解決糧食短缺問題。” 南方周末:您認為該如何提高目前中國農民的種糧效益?現行糧食補貼政策還需做怎樣的調整和改進? 袁隆平:有一次我們去驗收超級稻,有個農民跑來對我說,“袁老師,我看到你好高興啊!但是我們也有怨氣,你讓稻谷增產,可稻谷多了價格又下來了,我們還是不賺錢。”谷賤傷農啊! 我要提一個意見,一方面要出臺更多的惠農政策,要加大扶持的力度,最低保護價還要提;另一方面我建議糧食補貼的方式要改變,現在是按照畝來補, 種一畝田有良種補貼、農機補貼等,但是高產、低產給的補貼是一樣的,農民就沒有積極性。最好的辦法是,給與種糧農民按售糧的多少進行直補,即國家以較高的價格收購糧食,再以平價向市場供應糧食。這樣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就高了,因為他們所產的糧食越多,利潤也就越多;同時,市場上的糧價也不會上漲。 南方周末:您曾多次呼吁,發展糧食生產必須靠“三良”——良種、良法、良田,這其中的良種和良法都脫離不了科技人員的努力。但這么些年過去了,農業科技人員的待遇和境況沒有太大的提高;另一方面,現在的農業科技人才越來越不愿意下地了。您認為如何改善這一狀況? 袁隆平:雜交水稻研究是一項遠大的事業,需要代代有傳人。從1987年開始,我把多項獎金捐出來建立基金,資助科研人員。 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后,我從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為中國爭取到了生物學獎學金資助名額。有人擔心人員輸送出去不回來。我認為要把眼光放長遠點,只有把人家先進的技術學過來,才能把我們的技術水平提高。讓他們都窩到我的手下,受著我個人的思想束縛,怎么超越和發展呢? 研究中心隊伍30-40多歲的人都成長起來了,他們都能專心致志地搞研究。也有人總想往大城市跑,想升官發財,想下海做生意等等。人各有志嘛,不能強求。說句老實話,誰如果獻身農業,卻要想成為百萬富翁,或者地位很高的什么官,是不可能的。 但我要強調的一點是,我培養研究生并不太看重分數,就看他肯不肯下田。實驗室和電腦前的工作固然重要,但最重要的是下田,頂著太陽,趟著泥水,下田,實干,實踐出真知。培育新品種是應用科學,書本上、電腦里種不出水稻! 南方周末:作為一名農業科學家,您是如何看待城鎮化、農村空心化和農業發展的矛盾? 袁隆平:因為城鎮化,肯定有一些農民會失去土地。國家有政策會給他補償,補償之后會安排就業。我有一個更大的希望,是將農民從土地上徹底解脫出來,農民越少越好。農民多了,小康不起來。如果農民通過利用我們的先進技術使糧食單產大幅度提高,就可以在確保糧食總產量的前提下釋放一部分農村勞動力。我希望我國發展現代農業,至少讓50%的農民走出田頭。 南方周末:2012年中央一號文件里專門提到如何發展民族種業的問題,將之上升到了戰略的高度,但我國種業的發展情況并不樂觀,一方面種業公司多達一萬 家,小多亂雜;另一方面,國外的種子公司來勢洶洶,甚至已占有90%的蔬菜種子市場。您認為在現有情況下,種業發展在糧食安全問題中應處于一個什么樣的地 位? 袁隆平:種業國家把它定得很高——是國家戰略性、基礎性的核心產業,它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根本。這個種子,原來講是農業科學技術的載體,現在是農業科學技術的芯片。 值得注意的是,隨著農民種糧積極性降低,相應地影響到雜交稻制種業。2008年,雜交稻制種面積從2006年的150萬畝減少到80萬畝。這種形勢影響到 雜交水稻的種植面積,而雜交稻減少的話,那么國家糧食生產面積就得不到保障。糧食安全中有個種子安全的問題,種子安全中有個種子儲備的問題。國家要有 20%的種子作為戰備種子,以防不時之需。否則,遇到天災或其它風險,國家的糧食安全必將受到影響。